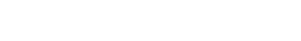“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北冰洋和尼罗河会在湿云中交融”|我和CCE的三年
发布时间:2026-01-2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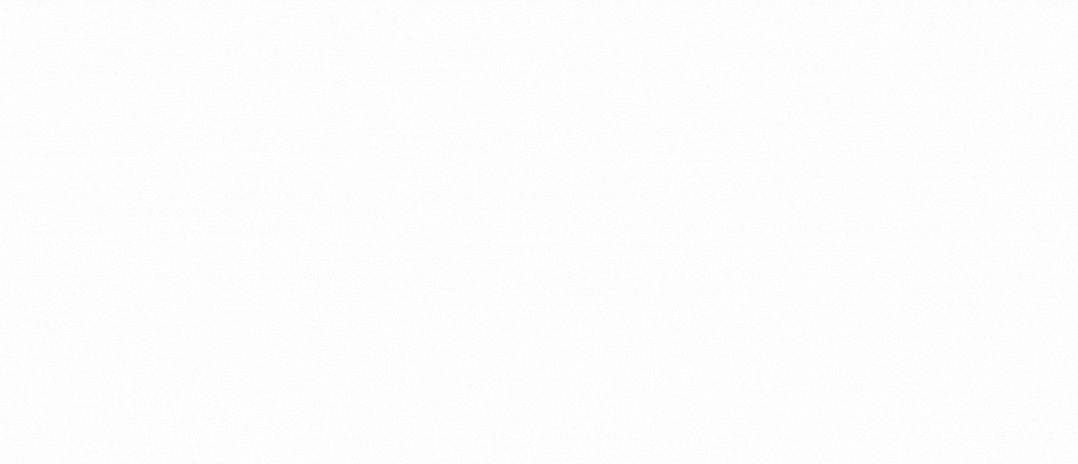

这篇公众号的开头,我想先介绍下自己。我想了好半天,怎么才能描述我,我想怎么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叫胡文瑞。2024年,我从常熟 UWC 毕业,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二? 好像太过平淡了。
于是,我换了一个角度去想:自我介绍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那我到底希望自己成为怎样的人?
想了好一阵,我意识到有一句话,我以前一直不敢说。但如果要赤诚地面对常熟 UWC 这三年的经历给我带来的影响,也许现在是时候说出来了。
那么,再来一遍——
大家好,我叫胡文瑞。
我是个导演。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来常熟 UWC 之前,我的世界都是小小的。
我来自浙江金华,一个因为火腿声名在外的小城。

小时候住在羊甲村,坐落在金华北山深处。
那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房子不多,更多的是鸡鸭鹅、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老墙,以及一年四季都吹着山风的小路。

大人们总在讨论物价、邻里琐事,再加上村口三三两两传来的八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声音,反而成了我最早理解“世界”的方式。
成长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的世界,起点往往是很小的。

但也正因为小,人反而更容易往外看。
山挡住你的视线,却挡不住你的好奇心。
余秋雨写过:“行走之外,心也在寻找更大的世界。”
而当一个人开始渴望更大的世界时,我也就开始了自己命运的迁徙。

小学之后,我就开始了“游牧”的生活,去了杭州,上海,考了很多学校,最后像是受命运驱使一般来到了常熟 UWC。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我和 CCE (Chinese Culture Evening, 中国文化晚会) 的初识却是一场意外。
刚进入常熟 UWC 时,我就被种类繁多的知行和活动弄得眼花缭乱:社会服务、设计、戏剧、体育……
世界一下子变得太大,而我还没学会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面试一个接一个,当时的我估计表现得很不自信,磕巴、不知所言,错过了好几个心仪的项目。
那时候挺难受的。不是因为非得进哪个项目不可,而是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擅长什么,或者是不是根本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所在的House-Heimat
眼看时间越来越少,社团的招新大部分都结束了,我收到了 CCE 招募导演的邮件。想着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又觉得自己还算有点文学上的造诣,我没怎么犹豫就报名了语言导演,属于导演组的一个小分支。
跟别的面试不太一样,CCE 的面试好像格外地正式,进考场的时候对面坐了一排导演主席,于是又很不争气地紧张了。
面试的时候我听见我自己僵硬地说着自己的经验,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彩,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直到当时的总执行 April 老师问我:“如果你的组员没有在预期时间内完成稿子,你会怎么处理?”
我想了一秒,然后说:“我会先问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真的写不完,那我会帮他们写。”
后来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显露“导演”的想法。
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态度上的,当集体出现缺口时,你是否愿意往前迈一步。那句看似普通的回答,成了我进入 CCE 的开始。
而我也在那个瞬间第一次发现,原来我并不是只在“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是真的在为一场演出负责。

“青灯有味,初识其明。”
第一年来到 2022 CCE 的时候,只是把它当作一场大型的晚会。
这是我第一次做导演相关的工作。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做什么都想先问问当时总导演 Yoyo 的意见。
语言导演主要的职责是跟主持人创作主持稿,负责一些语言类节目,参加节目的审核。原以为会做成一个服务行业,没想到却成了创作者。
“祈愿与祈福”这个主题出来时,我一时心血来潮,总觉得单纯的主持稿串场还是缺些什么。我提了一个小想法,想试着用一个小剧场的形式,用一颗许愿树,以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连起来。

当时只是随口一提,我以为这个提案会淹没在众多优秀的想法里,但大家没有拒绝,而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创作。
舞美组和导演组接力在 Common Room(公共休息室),花了好几周用钢丝拧出一棵许愿树,把节目的名字和大家写下的心愿一张张用红纸挂上去。

我和主持人们在教室天马行空地构思故事:马可波罗、乐队主唱、赶不上飞机的旅客、因为全球变暖无家可归的企鹅、在照相馆拍照的游客、在江南水乡初次相遇的陌生人、去店里修琴的男孩与老板、画不出画的唐朝老先生……

▲2022 CCE 与主持人的合照
我们用诗歌、戏剧、小剧场,去讲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想象,用一个个鲜活的瞬间,去解释每个节目的来龙去脉。自始至终,一群人在一起实现一个梦想的感觉总是让我再一次感叹,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2022 CCE 导演组与主席团合照
演出开始的时候,聚光灯打到那颗许愿树上。节目名、心愿、红色纸片在我的心里轻轻响动。
我站在一旁,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
“个体无法独自完成伟大之事,只有群体能赋予行动以形状。”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2023 CCE 全体演职人员合影
我和 CCE 的第二年,得益于大家的信任,成为了 2023 CCE 的总导演。
那年是很混乱的一年。
2022.12.12 疫情突然开放,学校通知可能会提前放假。
当时 CCE 的总监制李萍老师告诉我 CCE 要提前在一个星期内办完,不然就需要延期到二月份了。这个选择很难做,因为一切几乎都没准备好。可是如果需要延期,大家之前做的所有努力几乎都会白费。
发通知告诉大家这个消息的那天,微信群立刻乱成一片。
我坐在图书馆的角落,盯着那个不断刷新的屏幕,打好的话删了又删,删了再重写,最终发出来一句:“有空的人来图书馆一起讨论一下吧。”
来的人远比我想的要多,十几分钟后,图书馆的沙发边陆陆续续围满了人,几乎所有的节目负责人,导演组和老师都来了。
我很焦虑地说出这个情况,大家却没有展现出我意想之中的沮丧。我记得我的好朋友 Edward 当时对我说了一句话。“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们都无条件地支持你”。
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十分钟会议之后,大家做了个最勇敢的决定,我们准备一周内做完这个晚会。
晚会从那一句话开始变得真实。我们迅速重新分工、排调度、卡时间、定物料、改流程。当时中国舞负责人 Esther 跟我说,中国舞节目放心交给她们,让我安心去管别的事情。包括 China Band(民乐团),舞龙舞狮,Orchestra(管弦乐团)和各个节目负责人都有条不紊地组织自己的节目排练。
舞美导演 Kiki 和 tech crew(技术组)几乎跟我泡在剧院里,买道具、做舞美和设计灯光音效。
当时六位主持人和导演组聚在一个小教室里讨论主持稿,不知道是谁提了一句:“既然今年的主题是守护和拾遗,那不如就让故事发生在一个照相馆吧。”

▲和主持人们一起写稿
Kyrie 和 Isabella 说,我们中国舞中的山水意象,可以让“灵感枯竭的老画家”和“路过的旅客”来讲;
Jonathan 和 Barley 想到了《光辉岁月》背后的年代故事,把父辈的故事放进照相馆的墙上;
Zhengru 读了《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说这首诗的浪漫气质很适合照相馆的氛围;
Amelie 找来了高启的《咏梅九首》,说可以让照相馆像梅花一样留下痕迹。
那天晚上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合在一起,一个晚上写出了四千多字。

▲演出结束后,
导演组和主持人的合影
后来我们在央视春晚看到《再见照相馆》那一刻,所有人都有一种“押对题了”的荒诞感,好像我们的照相馆被世界回应了一次。
然而,演出最终还是延期了。

▲CCE被延期后,
我们导演组和主席团进行线上会议
2023.2.14,CCE 被通知可以正式演出的时候,在我心里,它已经不在于节目了。
谢幕看到大家一起跑上去的时候,我想着,如果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会被记住的回忆,就好了。如果 CCE 可以从文化的“代言人”,慢慢变成一台更加具有灵魂和热情的晚会,就好了。
2023 年的 CCE 充满了意外和挑战,但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年。
也许是行到水穷处,却发现我们并未走到尽头;坐看云起时,才明白故事正在重新开始。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第三年的 2024 CCE,我成了 CCE 的 Senior Consultant(类似一个高年级顾问)。
疫情已经逐渐平稳,国际生终于回到了常熟 UWC 的校园。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熟悉的文化语境,对他们不再“理所当然”。我们必须重新解释、重新翻译、重新寻找和研究。
主持稿更清晰了,节目更幽默了,文化讲述更国际化了。
那一年,CCE 超越了一场春晚,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交融。
如何让别人通过一扇门,走进我们的文化?我们到底想把什么留给世界?
 ▲2024 CCE预热视频的
▲2024 CCE预热视频的
导演组采访截图
我也变成了勇于做决定,果断决策的自己。站在台上谢幕的那一刻我很恍惚,对 CCE 的感动,和我身上发生的改变。原来我和 CCE 的三年就这样过去了,也变成传说中的 DP2 了。
说了这么多,但好像,这些对于经历的阐述,好像是永远没办法完全描述我心里对CCE 的回忆的。
就像 CCE 2023 结束的夜晚,我在旁边的戏剧教室里收拾道具。
盛大的演出结束后,我的心慢下来,真正地退一步去思考:CCE 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件事,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之后,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
中国文化晚会,到底是在追求什么?
我曾怀疑、困惑,觉得这场演出到底值不值得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觉得它能不能承受这么多人的期望与失望。

▲2024 CCE 主席团及导演组
想着想着,我发现,CCE 让我回忆的从来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是我在群里发一大堆工作分配之后的“收到”,是和主持人们一起编出一个好对白的激动,是半夜 Common Room 传出的欢声笑语,是联排时每个节目都准时到场的安心,是看到节目肉眼可见地进步时的激动,是听《光辉岁月》表演时一起挥舞的手机闪光灯,是开会时每个导演汇报节目进度时的认真,是每次联排和审核都从不缺席的李萍老师和主席,是说不完的感动瞬间。

▲2024 CCE,我参与中国舞表演《天浴》
那时候我总说,我们好像更像是战友,是为人们创造快乐的勇士。令人快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我非常荣幸能和这样一群充满热忱、专注且富有创造力的人一起共事。
海子说过,“人一生要见到许多闪光的瞬间。”
谢谢为 CCE 付出的你们,让我看到了我人生中众多最闪耀的时刻。

“循此苦旅,以达天际。”

2025年,毕业之后的我回国看联排。看到大家奔向台前谢幕的那一刻,我突然泪流满面。不是因为节目的质量,而是因为我看到这奇迹一般的传承。
李萍老师问我:“CCE 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
我说:“当然。”
和当初面试时一样笃定。
因为 CCE 从来不是一场演出。它是一扇门。
通过这扇门,我们希望世界的边界会因此变淡一点,文化之间的隔阂能消磨一些,人们对某个国家的误解能更少一些。
在莫欣·哈米德的《一路向西》里,他创造出了链接国度的任意门,只要找到能打开的那扇门,人们就可以去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每每看到此处,我就想着,我们也创造出了一扇门,一扇可以让所有人都通向中国的门。
就像“北冰洋和尼罗河终会在湿云中交融”,我相信那些看似遥远的文化、遥远的人、遥远的梦想,终有一天会在某种方式里重新相遇。
循此苦旅,以达天际。
穿越逆境,直抵繁星。
我和 CCE,大概一生都不会真正告别。
而我成为一名导演的旅程,也许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预祝 2026 年 CCE 圆满成功,也祝 CCE 在未来越办越好。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