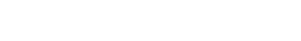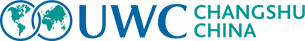“年轻时犯错比什么都重要”:从职校迷茫到镜头真实的探索之旅
发布时间:2025-07-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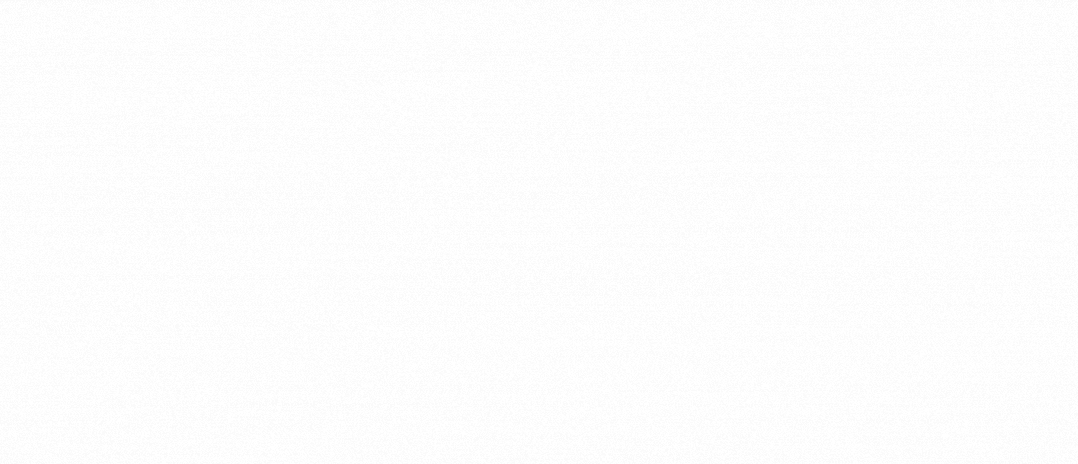

中考后,因为非本地户籍,她没能走进普通高中的校门,站在职校的门口,心里反复问自己:“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当这份迷茫遇见常熟UWC,她的故事有了怎样的转折?
从英国的大学毕业后,她为何不顾父母的质疑,辞去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一头扎进纪录片创作?班富俊(常熟UWC 2019届毕业生)的成长轨迹里,藏着她如何带着迷茫出发,在追问与行动中,让理想慢慢长出形状的答案。


2023年,在上海街头一间敞开的门窗安装工作间里,班富俊(以下简称Ban)的目光被吸引了。逼仄的空间内,竟悬挂着两幅《兰亭序》和《陋室铭》的印刷摹本,飘逸的字迹在油污工具间透出蓬勃的精神气。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纪录片的魔力,就藏在这些被忽略的角落,藏在每个普通人鲜活的生命里。这束照亮她镜头的光,其实早在多年前的久牵,就已悄悄埋下伏笔。

久牵:在迷茫里长出理想的嫩芽
2014年的上海,非本地户籍的身份像一道无形的墙,让成绩优异的Ban在中考后无法升入普通高中,最终走进了一所职业学校。
踏入职校的那段时光里,迷茫与不甘席卷了她:“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学一门技术,找份工作,然后呢?”这个问题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心头,却也悄然种下了一颗渴望改变的种子。
幸而,初中时加入的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窗。久牵自由探索、表达与创造的氛围,滋养了她对摄影、画画、读书和音乐的热爱。她将自己设计的绘画和摄影作品赠予他人,体验到“做自己”也能为社区带来温暖和价值。久牵的电影分享课,也成为了她影视事业的启蒙。当久牵创始人张老师向她介绍UWC时,Ban内心那份改变命运的渴望被点燃了。
首次申请UWC,因自我认知和目标尚不清晰,她遗憾落选。但Ban没有气馁,沉心反思,充实自我,第二次申请时,她拥有了更从容的心态:“如果不去UWC,会不会阻止我做想做的事?答案是不会。”这份坦然与成长,最终让她成功被常熟UWC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UWC:在鲜活的日子里探索热爱
2016年8月,Ban来到了常熟UWC。在这里,Ban找到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UWC鼓励学生开展社会服务,成为积极的“创变者”,这让她延续了在久牵萌生的社会关怀,积极参与孤儿院陪伴、艺术支教、动物保护等知行项目。

▲ 2017年,Ban参与Little Leaf知行,
在常熟孤儿院陪伴孩子们进行艺术创作、游戏等

▲ 2017年,Ban参与校园音乐剧《妈妈咪呀》
常熟UWC多元的环境和自由探索的氛围,让她确认了自我的表达是被认可的,个人喜好也能与社区互动并创造价值。
她曾回到久牵分享常熟UWC的生活:
在常熟UWC,Ban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分别是中文文学和视觉艺术,她都选了高级课程(HL)。在思考大学专业时,她发现自己喜欢文学、艺术、音乐,这三者她都不想放弃,这些结合在一起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指向了电影。

▲ 2018年,Ban与中文课同学的合影

“年轻的时候,犯错比什么都重要”
2019年,从常熟UWC毕业后,Ban带着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前往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的求学之路。在英国,她选择了电影实践作为主修专业,毕业后确定将纪录片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纪录片的创作允许她和社会中的人建立真实的联结,对她来说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加人文,也更符合她的个性和思考的创作方式。

▲ Ban在伦敦艺术大学与同学们合作电影拍摄
“我发现自己更喜欢社会题材,我喜欢将镜头对准真实的社会。对我而言,拍摄是一场‘乘法式’的成长——在记录中,我得以细细体会他人的人生,这也打破了我过去在摄影、绘画等个人化表达中那种艺术化的自我陶醉。当真正打开自己后,我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变得更全面,内心也更有力量,这个过程奇妙又深刻。而支撑我持续创作的,正是源于那份好奇心:想弄清自己是谁,拍摄的人是谁,以及他们为何这样生活。”
Ban的第一份纪录片工作是在复旦大学担任纪录片录音、导演助理和执行制片人。在工作过程中,她发现了自己的拍摄对象,一位来自江西的中年大叔——熊师傅。
熊师傅以安装门窗为生。Ban第一次见到熊师傅时,他的工作间的门敞开着,她看到了里面挂着的书法作品,在一方狭小的空间里居然藏着这样丰富的精神底蕴,Ban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通过采访,她了解到熊师傅对书法的热爱,他人对他的欣赏,并逐渐挖掘出他的故事:熊师傅一直对硬笔书法感兴趣,不断练习,直到有一天被上海书法家协会的徐老师遇见,从此开始真正的书法学习。
这段拍摄经历使得初入社会的Ban走出自己的局限,开始清楚地看见世界上的其他人,看见每个角落独一无二的生活。熊师傅面对生活磨难时的精神追求鼓励了她。
为了专注于创作,Ban甚至辞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
但纪录片创作从来不是坦途。找题材要泡在书里、新闻里,确定题材后要做海量调研;资金是难题,拍片子要跑多地,设备、交通、人员合作处处要花钱;拍熊师傅时,听不懂江西方言成了他们沟通的障碍。最磨人的是长时间的拍摄周期——一部片子可能要拍几年,怎么让最初的热情不被消磨?
“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Ban说。她学会了“不想太远”,把“我会不会搞砸”的焦虑放下,只盯着眼前的具体问题:今天要联系哪个受访者,明天要整理哪段素材,资金不够就去讲电影课、做讲座攒钱,听不懂方言就找熊师傅一遍遍沟通确认。

“把每一个你会面临的困难具体化,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然后你再去想办法解决它就可以了。”
起初,父母对她放弃稳定工作选择“折腾”充满不解。“这是一个说服的过程,首先得让他们看到我在努力,因为我觉得犯傻和犯错真的是很重要的,不然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适合什么,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去做,我一定会后悔,我不想留下遗憾。年轻的时候,犯错比什么都重要。”
她把自己的计划讲清楚,然后真的一步步去做——攒钱、拍素材、剪片子。父母看着她眼里的光,看着她说到做到的韧劲,慢慢从担心变成了信任。“我们家向来是谁有理听谁的,我证明了我是认真的,他们就支持了。”
在Ban看来,选择纪录片行业并非冲动,而是一种对生活本身的需求。拍摄别人的生活不仅让她感受到生命力,也让她从疫情后对自我的过度关注中走出来。疫情期间,很多人对自我的关注过分强烈,Ban发现,走出去拍摄外界,能够给她更多力量。
“我会问自己,你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虽然这条路很难,但谁的人生不难呢?我认为人生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即使不一定成为一个完全的电影工作者,我首先是一个生活着的人,而生活总是发生在记录之前的。”

连接与展望:用影像搭建对话的桥梁
Ban的纪录片创作也让她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于她而言,纪录片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而在不断与社会对话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些能够产生共鸣的朋友。例如曾在体制内工作,但后来因为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而转型的张老师,以及通过社交媒体普及纪录片知识的孙老师等等。
“做纪录片的这些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有些经验丰富的人会带领新手,不像大家刻板印象里的那样,‘社会对年轻人很苛刻’,人本身都是鲜活的,人和人的关系也可以是亲切且生动的。”
为了更好地推广影像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纪录片,Ban希望有机会能开展纪录片教育相关的活动。她深知,现代社会的青少年是在影像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但他们缺乏正确的引导,客观条件的限制更会引发表达的扭曲或极端化。Ban希望通过自己创立的“探映”这个平台,帮助青少年客观认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并通过影像找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她相信,影像是一种年轻的表达形式,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就像是一种语言的语法,而年轻人如何用这种语法去创造,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纪录片放映交流会,
促进创作者与观众的交流互动,图为第4期放映会
展望未来,Ban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她希望通过与独立纪录片导演、公益机构和影展的合作,让更多的人看到优质的影像作品。同时,Ban也计划学习更多美学和教育学领域的知识,与不同教育领域的人合作,逐步形成国内青少年影像文化的氛围。
她的目标是协助青少年通过影像与社会文化对话,勇敢表达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尽管国内的影视教育体系尚不完善,但她坚信,只要先靠民间的力量循环起来,未来总会有更多的可能。
从那个曾叩问 “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的迷茫职校生,到执起镜头记录人间真实的纪录片创作者,Ban始终在思考:自己究竟要过怎样的人生? 她用每一次选择、每一步行动,让心中的人生轮廓在前行里慢慢显影,而这份勾勒,仍在继续。
BanBan快问快答
1. 常熟UWC现在也有一群严肃的影像爱好者,你有没有想要给他们的建议?
2.在常熟UWC,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答:宿舍。和同学在学习以外有更多私人化的交流,很多时候袒露彼此的脆弱才是了解的开始。
3.为庆祝UWC常熟建校10周年,你想说些什么?
答:常熟UWC给了我探索真实自我的机会,让我更明白了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在和环境的碰撞中看到“自我”的形状。十年很长也很短,感谢这段回忆,也希望下一个十年,常熟UWC可以给社区带来更多活力。
文: 常熟UWC2025届毕业生魏一鸿对本文有贡献
图: 班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