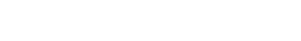从四线小城走进跨国银行的逆袭,让理想照进现实 | 我在UWC的故事
发布时间:2022-09-26
挪威UWC校园
我从挪威UWC毕业已有八年了,而近几年常常在最深的梦境里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挪威UWC校园。梦见自己站在学校的峡湾边上,看着因为海拔纬度高而颜色暗深的峡湾水,水里映着远处小岛上的松树和连接小岛的小木桥,远方的雪山还是那个依稀朦胧的轮廓。空气依然是像冰山水一样,既清澈又湿润,吸入一口,会觉得全身都被净化了,凉凉的,舒适的。
在梦里,有的时候我是回校访问的校友,从峡湾边上走那条碎碎的石子路,穿过student village (学生宿舍) 回到我当时住的Sweden House。有的时候梦到推开门,看到过去的自己和同学一起在common room (公共休息室)里喝茶聊天、烤蛋糕;还有一次,在梦里迷了路,找不到回宿舍的路,然后才回想起好像在Facebook上看到学校最近翻新了校舍,把原来摇摇晃晃有些年头的北欧特色的木床木桌换成了锃亮的钢管床,把小树林也推倒了变成了足球场。

挪威UWC的同学合影
但最多的时候是梦见自己又穿越回到了当时的自己身上,17岁刚刚下飞机到卑尔根,箱子里装着妈妈听说挪威湿冷就准备的新冲锋衣,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我那时刚刚从石家庄的一个寄宿高中离开,学校要求早晨五点半起床跑操,排队打饭要背古诗。然而飞机载着我,一下子就飞到了早八点上课、下午两点课就结束的挪威UWC。按当今的情形看,就是从万人过独木桥的“内卷漩涡” 河北一下子到了全民佛系与世无争的挪威。那时的我,就像一棵小树苗,原来在苗圃里和千万的其他小树苗一起长大,有着循循善诱的园丁打鸡血、定目标,总希望自己能长得更高更快更壮,才能获得更多空气、阳光和水。突然间小树苗被移植到了一块陌生的土地,土壤,气候,水分,还有阳光都和原来不一样了,最大的改变是园丁突然开始问这颗树苗,你觉得自己是一棵什么品种的树,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呀?
我刚开始的时候回答得斩钉截铁:我要考美国的大学,还要拿全额奖学金。挪威UWC的老师说:这很好,那你到美国的大学想做些什么呀?你平时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你觉得自己擅长什么?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想了想之后,我说我擅长数理化,因为在国内学过奥数,也读的理科实验班,分数考得都很高。至于喜欢什么,我原来很喜欢爬山也喜欢户外的空气和阳光,因为小的时候在太行山脚下长大,经常和父母去爬山,但是初中去寄宿学校封闭管理之后,就只在操场跑跑步了。老师说非常好,学校有数理化课,你也可以学些别的之前没尝试过的学科,像经济,西班牙语,环境学,挪威语。至于爬山和户外运动,老师指着不远处的峡湾、海岸和雪山说: “this campus can be your playground (把这里当成你的乐园)”。
我现在依然感激在挪威一次次跨出舒适圈的学习和锻炼。有些是自愿的,比如在英语还磕磕巴巴的时候又学了西班牙语和挪威语,在欧洲同学的注视下艰难得学着卷舌头发出R的颤音;又比如从小害怕速度和失重感却在滑雪周的时候深吸一口气从坡上滑下去,感受风吹过耳边,树林疯狂倒退的刺激,虽然知道按照这个加速度下去,大概率在下一个转角要用摔倒代替刹车了。可更多时候,成长的确来自于不期而遇的挑战之后。
挪威一个宿舍房间有五个人,学校一般安排每个大洲各一个学生,为的是促进大家进一步的文化交流。在中国寄宿的时候,大家都按学校的作息整齐划一,还有宿管老师检查卫生在熄灯后保持纪律,还都难免同宿舍学生因为生活习惯、性格差异发生小摩擦,让班主任和家长们头疼。而在UWC,学校却有意以宿舍为单位,搭起一个小小的世界,让我们在细节中学习和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朝夕相处。

作者(左二)与挪威UWC舍友在一起
刚开学的时候,大家都刚刚从自己国家离开,很难理解别的国家的同学生活习惯和诉求,难免为了一些小事发起争端。
刚到挪威的时候,我沿袭了原来晚上十点睡、早上五点半起的习惯,可是同宿舍的德国室友Mia却是全校最受欢迎的社交达人,喜欢在晚上邀请朋友来喝茶聊天,我常常挣扎着在明灯下勉强睡着,或者在凌晨两三点睡眼惺忪的时候突然发现宿舍里坐了十个人,秉烛夜聊得正起劲。开始的时候和Mia沟通并不顺利,因为在中国文化系统里,我认为高中孩子的睡眠时间和质量大于天,这关乎到第二天的学习和生活质量,而在欧洲文化里,社交文化却更重要,所以她认为UWC的意义就在于多和朋友们聚会交流玩耍。可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先是来自挪威的室友送了我一对耳塞,我难得睡了个好觉儿。后来寒假回国时,又专门按照床的尺寸做了一块遮光窗帘,这样无论我几点睡觉,也能把外界噪音和灯光的影响减到最低。
看到我的努力,Mia也开始慢慢改变,她看到我准备睡觉的时候就会把和朋友们的茶话会转移到宿舍楼的活动室,也会邀请我和她一起去参加学校的音乐会、话剧表演。后来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定下了每周五晚是roomie night (舍友之夜)。我们会一起准备茶话会的食物,有的时候是烤蛋糕,有的时候是热巧克力,还有的时候是大家一起从食堂攒的水果做的水果沙拉(挪威新鲜水果很贵,所以食堂的水果是每天一人一个)。参与者也从我们宿舍的五个姑娘延伸到了周围的朋友们,有一次,经济老师和西班牙语老师也来吃松饼喝热红茶了。
和Mia的故事只是在UWC很多通过沟通交流解决分歧的故事之一。工作以后,我常常遇到棘手的问题或者难缠的客户,却一直坚信着在UWC学到的基本原则:尊重、沟通。平等交流可以让我们平息一时的急躁情绪,理清问题的本质,然后和对方一起寻求解决方案。
2014年从UWC毕业以后,我有幸获得全额奖学金到Amherst College (阿姆赫斯特学院)学习。Amherst是文理学院,选课非常灵活自由。我主修了经济和统计,在专业课以外又辅修了政治科学,历史,心理等不同领域的课。我也把UWC培育我的服务精神从挪威带到了美国。我担任多门课的助教,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跟上队;我每周在学校的信息中心工作十几个小时,负责帮助教授和同学解决电脑技术上的问题;我跟着学校的宣传队学会了摄影,所以每次大会都有我架三脚架,扛摄像机的身影。在和学校的各个部门一起努力把学校变得更好的过程中,我跳出了自己作为学生的思维框架,对自己的大学体验有了更深的感激和认识。
这是我在UWC学会的一点,一个有爱的集体是需要每一个成员去努力维护的。除了教课, UWC的老师经常身兼数职,更像是在教我们如何在一个社区里面尽自己的能力发光发热。
从Amherst毕业之后我如愿以偿去了纽约的华尔街做投行。去华尔街做金融一直是我的梦想。我想通过金融,来帮助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企业成功转型,找到和环境和谐相处的途径。毕业后我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帮助危险废物处理公司收购一个负责在海上清理漏油的公司。这个并购造就了美国最大的危险废物处理公司,而我通过和公司的合作,在垃圾车,处理中心,和填埋场的数据中,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垃圾对环境的压力。我想起和挪威的host family (寄宿家庭)一起在他们的循环农场里用厨房残渣做有机化肥。当时的我虽然觉得很有趣但是却不能完全理解住家妈妈为什么会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在自家堆肥。每一个香蕉皮或者蛋壳,每一个盘子里的残渣都被认真收集到小桶里等待缓慢的发酵过程,直到它们变成后院好看的玫瑰花的肥料。
三年投行之后我在今年夏天加入了一家投资公司,依然专注于环保工业,在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同样关注对环境的影响。工业占据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每一个工业公司的一点点进步,可能是更节能的机器,或者是更清洁的能源,再或者是技术层面的提升,都会让我们离可持续发展近一步。工作中我执着于思考如何加速工业绿色化,生活中我的生活方式也慢慢发生改变。想到美国塑料回收的产业链还不成熟不完整,导致大部分塑料都会被焚烧处理,我伸向一次性水的手就缩了回去;想到食物的生产和运输耗费了大量能量,我对冰箱里的蔬菜水果保证,一定让它们善始善终绝不浪费;想到快时尚导致的过度购买和环境压力,我省下了不少逛街的时间和金钱。UWC的使命是为了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我希望贯彻这个使命,不多去占有不必要的资源,让地球养育我的压力越小越好。
UWC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好的机会和眼界,更重要的是UWC在我心中埋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如果你在对人生观有奠定意义的17-19岁的时候,见证过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同学们欢聚一堂,为了心中的目标一起合作一起努力,逆境就很难磨灭心中的希望的火苗。这个理想主义常常让我发问,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谁会呢?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挪威老师这句话,把学校当成乐园是我理解教育真正意义的开始。在之前的中学,每次考试都要年级三千人大排名,贴大红榜,每次考试之后要立新的目标。我对未来有好多美好的畅想,想去很远的地方上大学,想去看不一样的风景,可是在沉重的压力下我没有力气想那么远。我得集中精力做一张一张的试卷,期待着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以为我在收到UWC录取通知那一天会毫不犹疑欢天喜地地告别高考。可事实上,从三月收到录取通知,我直到五月份才离开学校。在这两个月中,从爷爷奶奶的坚决反对,到父母对未来的担心和不确定,从学校老师和同学的不理解,到我对自己的怀疑。已经在高考这条路上准备了十一年,突然换赛道再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国外申请有竞争力么?UWC的奖学金只有两年,如果拿不到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怎么办?周围有太多的声音告诉我出国是富裕阶层家庭从小帮孩子规划的道路,对于工薪家庭,学习刻苦的我,最适合的还是高考。可那时的我觉得是金子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光,机会一定会眷顾肯努力肯冒险的人。家境会决定失败后的底线,但我宁愿尝试过努力,头破血流后哪怕回到高三重新开始。我害怕的是让当时受限的眼界影响我的上限,害怕多年以后去回想如果当时上了去挪威的飞机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常熟UWC董事赵宾老师。在我父母犹豫不决的时候,赵宾老师一次一次地打电话,解释UWC的理念,传达UWC中国国家理事会对我的信心,劝说他们多和当时还在寄宿学校的我多沟通想法。是赵宾老师的第五通电话感动了爸妈,他们放下电话就请假开车去石家庄接我出来,决定尊重我的想法,让我去UWC试一试。
UWC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感激当时的自己,虽然我来自四线小城邢台,即使中学去了石家庄,自知机会仍是万里挑一,但是勇敢地把自己对UWC的向往转换成了行动。我感激我的父母,在UWC还在国内不知名的时候,不顾爷爷奶奶亲戚朋友的阻拦,坚决支持我的梦想。我更要感谢那些在我追梦路上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师和朋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前进的鼓励和自信。
所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和当年UWC面试时认识的好朋友段孟宇(段孟宇的文章链接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一起创办了 UWC Bridge Program,来帮助已经被UWC录取但因为环境受限英语基础较薄弱的学生。我们每周上课,一起读书并讨论心得,举办辩论赛,学生们还自愿在感兴趣的话题上做演讲分享。段孟宇来自蒲公英学校,后来去了英国UWC,她对教育的热情让她从英国到了哈佛学教育,又从哈佛回到了她热爱的蒲公英学校当一线教师。回想起我们在十年前面试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英语都是一个个单词不连贯地往外蹦,而现在我们两个带着新一代的UWC学生,一起探索和成长。

我在挪威UWC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每个UWC的毕业生在UWC的体验也都不一样。UWC就像一个大宝藏盒子,有着丰富的资源宝藏等着你主动挖掘,助你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UWC也像一面镜子,它会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和脆弱,欲望和野心。UWC不是一个魔术旋转门,不是每个人迈进UWC之后都能自然而然地找到热情和理想,走上人生巅峰。就像没有一夜长成的大树,所有UWC带来的成长都来自历程中风风雨雨的洗礼。
两年在UWC的学习和生活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帮我从个人的“小我”中跳出来,以一个观察者、学习者的身份去聆听别人的故事,去关心除了自己的荣辱浮沉以外的更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UWC督促我在生活中成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周围的环境任其摆布。
在离开UWC的这些年里,每当我因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会回想起当初那个对未来一无所知但是勇于接受UWC挑战的十七岁的我;每当我被竞争和内卷压抑着感觉透不过气的时候,就会想起UWC来自世界各地同学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热爱,提醒自己人生有多种打开方式,但既然因为热情和勇气选择了现在这条路就要坚持下去!离开UWC以后,UWC更像是我内心的伊甸园,那里珍藏了我最初的梦想和最无畏的勇气。我常常会在梦里回到挪威这个200人的小村庄去看看,那里是我心里温暖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