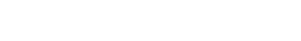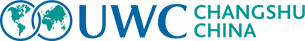波黑UWC的那个秋天|冲突和理解
发布时间:2020-11-09“你怀念铁托吗?”
“我有点怀念,至少那个时候我们都有工作,我的父母有,现在他们只有一个有工作。内战导致了太多伤痛。包括民族仇恨的集中爆发,种族仇视,宗教冲突,到现在仍然在主导着巴尔干半岛。”
这是我与波黑UWC物理老师的交流。

波黑UWC的秋色
我曾经和许多人提起我所在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他们会有两个反应,一个是问我波黑在哪里,安不安全。第二种会问我是不是前南斯拉夫,然后会跳出关于铁托、一战导火索等等的记忆,老一辈或许还会唱起《Bellaciao》。
的确,欧洲火药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的,不说萨拉热窝的普林西波,也不说巴尔干在东欧剧变时期的政局动荡,只说我住的莫斯塔尔(Mostar)的老桥,断了又重建,就演绎着波族和塞族的恩恩怨怨。
我住在Mostar,一个盆地地形的,波黑第五大城市,虽然南北间距只有10km,比中国一个地级市都小。这里,是我上学的地方,生活的地方,成长的地方。

老城风景
这里曾经是内战的前线,波族和赛族军事冲突的前沿,枪炮,犯罪,在二十年前是这里的常态。从我的宿舍susac走三公里到学校。于是乎,这样一个特殊的学校,特别的城市,构成了我这个口中名副其实的江湖,江湖充满了冲突。
走在老城那坑坑洼洼的石头路,我背着滑板,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坐在老桥旁边,看着跳水的人索要奖励——这是他们辛苦应得的。和我的co-year一起,一位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男孩,吃着牛排,诉说着各个国家不同的见闻。我们从阿尔巴尼亚的毒品泛滥; 从欧洲的集体右转,聊到现在欧洲的难民政策。世界局势似乎离我们很近,近到ISIS的攻击会让我们同学的家人丧生,近到伊拉克游行导致的管制让我的同学联系不到家人,近到美国对于穆斯林的管制让我的同学得到了offer也无法去上学;近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同学互相排斥,近到,全世界就是一个小江湖。
江湖有故事,故事特别多。
文化冲突在这里无处不在,波黑的街头艺术,1994的战争尾声字样无处不在,我在思考,如果当初铁托继续活下去,巴尔干的局势到底会怎样。人们都怀念铁托,因为铁托是个好人。当我唱起Bellaciao时,总是有人上前来。“兄弟,你也听这个啊。”波黑人的身份从来没有改变,上世纪的风云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心中。怀念铁托并不是一味的去止步不前,而是要告诉现在的国家,现在的领导人,应该怎么去做。
还是坐在老桥旁,我喜欢讲故事,也喜欢听故事。我听到的故事包括但不限于今天又吃意大利面的抱怨,我的同学如何怀揣着理想主义去帮助难民,小到各种宗教的细节,大到国家的恩恩怨怨,我都听到了。
“朋友,你为啥不去西欧玩?”
“西欧的政府不让阿尔巴尼亚的未成年人单独出行,因为总有阿尔巴尼亚人想黑在西欧。”
一个简单的出行,却映射出了地区的政治生态。
“咱们去老桥玩玩。”我拿着滑板,和co-year一起走到了老桥,面对着清澈但暗流涌动的河水,我在想,很少有人在这样一种地方,这样一种学校,就如这河水一般,充斥着冲突,但表面却风平浪静。“巴尔干从来没有和平,我们波黑人不信和平。”这是我的波黑同学的原话,这印证了我的想法——巴尔干没有和平,巴尔干也没有战争,就现在而言,巴尔干在战争与和平之中,这是一个江湖。
江湖也存在着平静的时候,理解有时能抚平一切波澜。UWC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将矛盾和冲突放在了一起,矛盾和冲突会慢慢在碰撞中交融在一起。
在学校组织我们去难民营做义工的七天,我听到了很多故事,也见识到了什么叫真实的conflict(冲突),还有在欧洲难民问题严重的状况下的政治观点冲突。

作者(右五)在难民营
我具体了解了一个会说英语的家庭,他们是从尼泊尔逃离过来的,他们的护照被土耳其政府扣下,相当于没有国籍的难民。我向他们询问了关于他们的未来问题,其实他们还是挺喜欢波黑的,因为当地的政策比较宽松,而且对于难民也比较友好。他们的女儿由于是生在难民营的也自动拥有了当地的国籍。有些从阿富汗来的难民不会说英语,于是只能靠我的阿富汗同学来翻译。有一家分散在三地:阿富汗、德国、波黑。她告诉我们,她想去德国,但护照也被土耳其政府扣下(土耳其锅),只能去政策比较宽松的东欧,她有亲戚在德国,但碍于德国严格的政策,她无法前往,而相对混乱的阿富汗,她也没有足够的钱把她的丈夫和孩子接过来。当时我的德国同学就说了一句:“我的政府都疯了,他们居然觉得应该用枪去射击难民避免他们偷渡。”

UWC day
我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难民问题,尽管自己以前也在想欧洲是否有义务帮助难民。虽然欧洲自己也有自己没有解决的问题,抛开这个问题,我确确实实地觉得应该进行人道主义的帮助。
为什么我说现在欧洲是右翼保守势力抬头的欧洲,是民粹抬头的欧洲。很大程度上就是欧洲对于难民问题的争论,比如对于难民严苛的政策、难民涌入导致社会压力过大、难民进入后产生的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再加上原有的认为欧洲自己没有义务帮助难民的右翼势力成为了一种趋势,使整个欧洲看上去有那么多的冲突。
我身边就有例子:我的亚美尼亚同学对于学校组织的项目周产生质疑,他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更多,持续性,有计划性,而不是就做这种短期的项目周。我的一位德国籍同学则认为我们虽然做的很少,但我们也帮助了他们、影响了他们。比如孩子们终于有了玩伴——因为很少有人能陪他们玩。“让七天变的有意义,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后来,他们的讨论从项目周本身提升到了对于欧洲是否有义务容纳难民这个问题的争论。亚美尼亚同学觉得无限制地容纳难民会增加社会问题和负担。而德国同学就一直在批评自己政府的不作为,觉得人道主义援助不够积极,毕竟欧洲离他们那么近,自己也有义务维护难民的人权。
我这次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欧洲左翼和右翼的纷争,一个真实的欧洲,一个左翼与右翼齐头并进的欧洲。也许我的同学们并不知道怎么定义左翼右翼——就算他们是欧洲人,可能也不知道左翼右翼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圆桌会议的位置安排——但他们知道,我们在项目周所做的是在维护着公平和正义。
中国距离欧洲很远,距离难民问题很远,中国的民族构成也没有外国那么复杂。欧洲现在基本上是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并存,大量其他地区的人涌入欧洲。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真真切切的感受到难民问题的急切和危机。我只能说,面对着这些“小人物”,我只能默默祝福他们能顺利地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也希望欧洲不会因为难民问题变的不是以前那个欧洲。
理解之后也是反思,我也在反思自己所经历的教育体制。在和我的阿富汗同学交流的时候,她这样评价道:“你为什么要来UWC学IB,你们的教育体制那么好,那是现代教育的标志。”我想了想,可能是在不同环境下成长的人,对于同一样的事物确实有不同的评价。“你觉得我们的教育好吗?”我问。“我觉得挺好的,那就是你们为啥有钱的原因之一。”我笑了笑,没说什么。这让我在想起,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辩论,或者说就业导向和学术导向的辩论。我经历了中国严格的学术训练让我拥有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在UWC的IB学习经历也让我学会了一些在中国教育体制中学不到的东西。所有东西都需要辩证看待,这两个教育体制在塑造学习者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打上它的特色烙印,这两个体制都有其合理性和不足。我无法评说这两个体系的功过,我只能说,我感谢这两个体系在我三观和成长的重要阶段给予我的重要精神财富,是他们让我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人。
有时候我在思考,在这样一个年纪去往这样一个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学校学习,我是否做对了选择?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我做出了选择,让我的人生从此是另外一番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