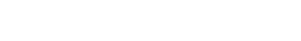UWC是一所我永远毕不了业的学校
发布时间:2017-05-04在UWC度过的两年时间,到底对我后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没有在从政、做社会企业、人权律师、绿色和平、或用其他典型“热血青年”方式在改变世界的我,跟一个没有去过UWC的人,有何不同?
卜婷(Hedy Bok)是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的毕业生,2007年IB状元 。
被多家美国顶尖大学以近全额奖学金录取,包括普林斯顿大学、达特茅斯学院、芝加哥大学、卫斯理女子学院等。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专业以及电影专业。
生于江苏,长于香港,现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研究宗教与艺术。曾为记者、新媒体顾问、演员及专业翻译。文字与多媒体作品可见于《南华早报》、《明报》、《Shanghaiist》、《Asymptote》、以及个人YouTube频道。她在UWC毕业十周年之际,特撰写此文,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UWC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香港的UWC毕业十年了。身处美国读研究生的我,正经历着不同的争论和冲突。特朗普反对墨西哥和穆斯林移民的政策,让许多大学同学愤慨难平,有朋友直接翘课去游行。看着不同种族的人在努力彼此理解、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每每失望,却又屡败屡战,才发现原来我从未离开UWC。
在UWC度过的两年时间,到底对我后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没有在从政、做社会企业、人权律师、绿色和平、或用其他典型“热血青年”方式在改变世界的我,跟一个没有去过UWC的人,有何不同?“促进跨文化理解,推动世界和平”是专属UWC的理想国口号吗?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个80后毕业生对她“UWC后生活”的真实思考和体会。这也许会跟你想象中的UWC毕业生的生活状态不一样,也可能正是你想像的样子。 (我个人并不代表一个群体。UWC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也非常不一样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困惑想跟我聊聊,欢迎留言分享。)
到底这所奇葩的学校除了让我的青春过得好玩儿难忘,又提供了绝佳的出国升学平台以外, 它有没有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抽象崇高的东西先放到一边儿去。我先来说点实际的。
“吃喝玩乐?”
对,就是吃喝玩乐。
除了跨国友谊和IB课程培养的独立思考能力外,有时候我觉得UWC在我现在生活中最真实的存在,就是我的音乐播放列表。里面有冰岛的独立音乐,爱尔兰的凯尔特民谣,印度的拉格,牙买加的雷鬼,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音乐,东正教圣乐…...而很多这些乐曲,我都是在UWC时第一次听到的。那时大家都喜欢在线上共享音乐,而我们几个室友也喜欢翻翻别人的音乐,看看大家都在听什么。(当然,很多音乐也是被强灌洗脑的,就如那首开趴必点的拉丁high歌Gasolina…...)原来只听广东歌和英伦摇滚的我,慢慢喜欢上宝莱坞和泰国摇滚。
另一个UWC在我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就是我的饮食习惯。我什么国家的东西都喜欢吃,而且是味道再特别的都爱吃。我必须感谢为我打开味蕾的UWC同学们,每次放假总能让我吃到土耳其的各种果仁、挪威的焦糖味干酪 、阿拉伯苦得像中药的咖啡、泰国的方便面。高中两年,我也学会了如何混搭民族装、爬树、跳水、抽水烟(这是一种中东习俗,不是“学坏”!)、读伊斯兰诗歌、跳舞…...

卜婷最爱的蒙古餐
这一切,听起来都是对其他文化非常浅层的接触,却唤醒了我对世界的好奇,让我思考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很多文化中的丧葬音乐都是节奏缓慢而悲伤的,新奥尔良的黑人葬歌却是欢快明亮,甚至带点嘉年华风的呢?闲时,我爱喝印度拉茶、吃北非料理、焚乳香读书、敲頌缽静心、研究古爱尔兰信仰,即使是独处时,也从不觉得无聊。我没有刻意把我的生活设计得如此“多元”,而是上学的时候眼界一打开,就自然对很多东西产生了无尽的好奇和喜欢。
那会玩会吃有什么用呢?
吃喝玩乐,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是“外圈人”和“内圈人”的区别。当我能够融入一种生活文化,就已经代表着某种社交上的连接。
如果一个外国人除了会说中文,还能吃臭豆腐,喜欢鹿晗和吴亦凡,那估计她在国内交朋友、说不定做生意上都会比较顺利。同样的,如果我什么异国料理都能吃,什么音乐都喜欢听,那我无论到哪里生活,遇到哪些人,都可以很快地融入。
现在大部分公司都有海外业务,哪天被公司派去泰国做个半年的项目也是常有之事。 对某个文化的物质和精神面有过初步的理解,并不代表说我就天下无敌,不需要适应和融入,而是我会能够更快地找到生活的平衡,更容易认识当地的朋友,也能更深切地喜爱这片土地。

作客上海外语频道,谈女性在东西方社会的角色
吃喝玩乐,是关系的起点,聊天的基础,友谊的催化剂。在多元、全球化的世界里,你永远不知道要跟什么人打交道。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某纸媒当记者。当时因为公司刚开始做新媒体,我们几乎什么新闻都要做:政治、社会、教育、娱乐、财经等,每天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不同的采访对象身上争取取得最多的信息。可能上午还在跟一个英国的设计师讨论时装周,下午就要去找菲律宾雇佣组织了解劳工被剥削的现象。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在这些情景上都能大派用场。跟采访对象聊聊菲律宾电影和音乐,关系马上破冰。
吃喝玩乐,更是一种情怀。有些人可能觉得嗜好只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古人更云:玩物丧志。我却认为它们是精神财富。试想,光是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文化财富,让我们学会欣赏琴棋书画、吟诵诗词歌赋、徜徉于山水之中。要是我能同时培养对其他文化情景的鉴赏能力的话,我的精神生活会多么得丰富啊?
物质文明是一个民族历史和价值观的载体。世界那么大,人文宝藏如此丰富,而我就像是个亿万富翁,有着没人可以夺取的财富。是UWC给了我“第一桶金”。
身份认同
讲完好玩的,讲点抽象的概念:身份认同。
李萍老师是我们IB中文的老师(李老师现任常熟UWC副校长),大家都非常敬重她,最近有同学还拍了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在UWC这种国际学校的环境中,李老师经常叮嘱我们香港和国内学生说:“You have to be national before you can be international”——必须先有“国”,才能有“国际”。

与李萍老师合影
在UWC的第一个学期,我觉得李老师这句话有点多余。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同时也跟其他国家的同学玩得很欢,简直是又有国,又有国际。
可是很快, 我就迷茫了。
有一些同学,习惯用肢体表达友好,每次见面都要亲好几下的,我要不要也跟随这样子的社交方式?我可以在尊重他们文化的同时,又保有自己的底线吗?有一些同学非常热衷维权运动,那我是否也要为了加入他们的讨论开始反对一些我原来支持的“保守”立场?一些习惯表达自己意见的同学经常在课上高谈阔论,那我是否也要为了说话而说话?
沉默到底什么时候才是金?
这些文化碰撞让我不断思考:到底我是带着多少(我主观定义中的)文化信条在生活的?作为一个香港人,我觉得我需要每天进取,高效率地做好所有事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是谦逊,爱读书的,想有一天让父母过上更富足的生活。作为一个国际学校的学生,我应该能够自信地呈现自己,关心时政,把理想放到第一位。 每种文化都代表着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套做选择的原则。本来价值观就有点冲突的我,面对这种UWC这种多元盛宴更是手足无措。

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中国文化晚会
可是也正是这种混乱,让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作为一个在国际环境中生活的中国人,我的首要责任并不是“成为一个世界公民”,而是先“成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了解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传统价值观的中国人。成为中国人不代表我就要去盲目爱国,认同所有中国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也不代表我要每天穿唐装用国货。而是当同学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吃粽子”、“京剧那么刺耳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听”、“你们有没有神话”、“中国是否尊重女性”的时候,我可以有根有据地分享我的见解。
当其他国家的同学都能够滔滔不绝的介绍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时候,我能够同样详细地介绍中国,是回报他们的慷慨,也是对自己的基本尊重。
我在美国大学本科学西方经典时,一开始还窃喜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可以用我的第二语言英语去读本地人都觉得晦涩的书。可是当我看到美国同学讲到古罗马历史时,那种热情和归属感(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是颇为复杂的问题,在此不深究。这位同学自认是古罗马的传人。)让我想到我对国学极度浅薄的理解。上文言文课时就更是惭愧,多少美国同学的古汉语都学得比我起劲,谈论着我都搞不清楚的《论语》。我发现,在没有国学基础的前提下研究西方文化的我不但没有底气,更失去了一种可贵的比较视角和创新的机会。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日
当我更了解中国,我就能够看到我们与其他文化的相似之处。有更多的相同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就会有更稳固的基础去处理并包容差异。在人际关系中如是,在外交关系中亦然。
哲学家Paul Tillich说过,"The boundary is the best place for acquiring knowledge." “边界就是最能够获取知识的地方”。边界是一个领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领域的开始。所以处于边界的人往往能够从差异中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并理解事物在表面矛盾下更深层次的共性。现代中国如胡适、林语堂、许地山那样的思想家,又如当代的余英时、李欧梵等学者之所以如此有影响力,也是因为他们能够融汇中西,学贯古今,拥抱“文化边缘人”的身份。
当然,我并不完全是我的文化身份,我也不只是中国人。但是在一个多文化的情景中,当我是唯一能代表某个文化的人的时候,我的文化身份就会被放大。在美国,朋友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一般不会说“喜欢济慈的Hedy”,而是“中国来的Hedy”。当我在会议上一言不发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Hedy很沉默”,而是“那个中国女生很沉默”。
身份认同是个有机的自我觉知,而且它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有些环境会要求你变得跟身边的人一样,有些环境要求只要表面功夫做足就好,有些环境就是鼓励你的独特性,不希望你跟别人一样。
在这些环境中,无论我要选择成为、模仿、还是理解他人,我都需要先清晰知道我有哪些界线 。
我个人的一个底线,就是我再欣赏美国文化和环境,都不会放弃我自己带来的中国和香港文化。

采访香港点心师傅的短片
当然,如果我直接模仿美国同学的生活习惯,努力看他们喜欢的电影和球赛,聊美国政治,只是围绕他们熟悉的话题来聊天,那样交朋友会容易很多。我以前也曾经这样做过,但是那样的我,是虚构的。
现在的我知道那样的关系并不对等。
当“我们”这段关系中只有你的文化、你的喜好、你的价值观,而没有我的部分的时候,这并不是友谊,而是我在带着我的自卑在讨好你。 如果我不能尊重自己,别人如何尊重我?
李老师说得对,想要走得更远,先要知道家在哪里。UWC的经历一直在提醒着现在的我:想要建立深刻、真实的友谊,必先记得自己是谁。有了“我”,才能有“我们”。
人格理想
申请UWC的时候,文书上面有一个问题是:“你最想改变什么?”当时16岁的我,觉得肯定是要写什么希望世界没有核武器啊,海洋没有污染啊这种听起来很有理想的答案才好。但是后来有一位在UWC 的学姐提醒我说:“只有可以今天就开始实践的理想才是有意义的。”我想了很久,就在我的申请表上写了:“我想每天早上在电梯里看到邻居的时候主动向他们打招呼,而不是假装没看到对方。”
我并不知道当时阅读我的申请文书的老师们对我这个微小的“理想”有何看法,但是学姐讲的那句话,我至今仍然受用。
在UWC时,我们宿舍每周都开会,就群体生活上的一些事务提出想法并一起讨论。让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有一次有几个同学开始在热烈地争论到底每个人洗完手之后要用几张抹手纸。事情源于一位很关注环保的同学看到有人洗手后用了三张抹手纸来擦,然后就很生气,吵了起来。争论中,大家经常会说“你这样太不UWC了!”或者“作为一个UWC学生,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老实说,那时候我非常厌烦这样子的周会,总觉得小题大做,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问题等着我们来解决,干嘛要浪费时间讲抹手纸!
到了二年级,有同学们开始抱怨香港学生抱团的情况严重(LPCUWC那时候有一半是香港人),而且普遍注重考试,对升学没帮助的活动几乎都不太参加,仿佛浪费了在UWC的机会。香港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的分化日渐明显,这在食堂这种公共空间最能够体现:几桌讲广东话的香港人,几桌“美、加、英、纽、澳、南非等”这些讲英语母语的人,一桌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几桌英语讲的不怎么好的其他国际学生。当然,我也是“广东帮”的一员。
一天,临近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香港同学又坐到一起吃午饭,正聊得高兴,有一个意大利和一个爱沙尼亚的(印象中还有两个人,抱歉我忘记你们是谁了)同学“啪”的一下带着餐盘坐到我们中间,叫我们换频道讲英文,然后开始问“告诉我你们中国人是如何庆祝新年”之类的刻板式问题。我一看周围,其他“广东桌”也有国际学生同时加入。同学们在用近乎集体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不满了。关于节气习俗之类的“谈话”生硬地进行了一顿饭的时间,几位比较礼貌的香港同学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我则一言不发,只觉得有好多话想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想去联结,又仿佛觉得被指责了。
他们的意图是好的,进行的方式是粗暴的,我们的回应是肤浅的 。一桌母语都不是英语的人用英语在进行着极为别扭的“文化交流”。那是我吃过最痛苦的一顿饭。
作为一个群体,香港同学被教训了。而且在我看来,甚至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无可否认,香港人的确比较认真读书,而且都务实,表面上看,好像很多学校的社会服务活动、学生会议等都不经常参与。但是,我知道很多同学其实背负着巨大的家庭期望和学习压力,并不能,也不想像一些同学那样完全“自由发展”。
那为什么要讲广东话,让其他学生都听不懂?我只能说,作为经历过殖民时期的香港人,我自己是不愿意与香港人在一起的时候讲英文的。那对我来说是殖民语言,是跟外国人交流时候用的语言。在这个后殖民语境下,英语讲得好的人会显得更聪明、更有想法、更有尊严。这样的世界是扭曲的,因为很自然地,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就能够有更多文化影响力和舆论主导权,从而获得更多“软实力”。
但英语已经成为了通用语言,这是不争的事实。那如何可以在维护民族尊严,和促进跨文化交流中取得平衡? 如何可以让那些不愿意讲英语,或者英语讲得不好的人在国际平台上也有表达自己的机会,而不是被后殖民语境限制了话语权?这些不单是UWC的难题,更是全球化时代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挑战。

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毕业晚宴
理想中的UWC,应该是每个人相亲相爱,无分国界地“手牵手、心连心” 的。但我所经历的UWC并不是理想国。它就如真实世界般复杂、破碎、充满历史和政治的包袱。
UWC跟真实世界唯一不同的,是它会有更多愿意去尝试解决问题的人—— 如那两位突然坐下来跟我们“聊天”的同学(尽管方式可能比较特殊)。 我知道学生群体之间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也不是UWC独有的问题。不过我也很清楚,所有误解的源头都是因为缺乏清晰的多方沟通。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如UWC、如香港、如美国,同一个文化或种族的人是否不应该“抱团”,多点去跟与自己不一样的人连结?理想的社会是否就是完全共融,没有小圈子,没有疆界的社会?
面对如此复杂的议题,二年级的我没有头绪,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所以就做了我唯一会做的:把想法写出来,发到校报上。国际学生已经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感受,而我想提供一个作为香港人的个人观点与回应,分享另一边的声音。文章内容大概就是我上面讲的,发出来之后收到很多同学的电邮回应:有表达理解的、有困惑的、有感动的、也有想找我当面辩论的。
憋了一肚子的话,终于讲出来了。我们的声音,彼此都听到了。
回想起来,这算是我第一次主动对文化矛盾做出回应,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发声”的力量。跟讨论擦手需要几张纸一样,在校报上写一篇文章解决不了任何人类难题,但是对于发声的人来说,表达自己本来就是一种勇气和希望的累积。多一个人延续某个话题,就多一些人会去关注。关注的人越多,讨论内容的达到一定的信息量,就能开始影响舆论方向,从而带动价值观的质变。
后来在媒体工作时,每当我开始质疑自己工作意义的时候,总会想起“食堂事件”,鼓励自己:声音微小不要紧,正是声量不大的群体,才须要更多我这样的微小声音。

做记者的生活
当然,目睹不公义的时候,也时常胆怯。多少事情,往往一个“忍”字,再加一个“忙”字就把自己给忽悠过去了。但是UWC的那一桩桩“小事”总像那关不掉的自动播放歌曲一样,提醒着已麻木的我,事情的另一个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我学习到作为社会个体,我的责任不是去抱怨我改变不了的事情,而是去想想我今天能够开始做哪些“小事”:忍受不了雾霾,就多坐公交车;不喜欢别人对服务员呼呼喝喝的态度,就自己对他们多友善一些。
TA就是你
我曾经在国内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实习。酒店的经理对我很照顾,希望我可以有更全面的学习,就让我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体验一下。而其中一个岗位是顶楼餐厅的服务生。
端盘子不是我的强项。第一个礼拜每天都很紧张,害怕会打碎高脚杯,怕漏了给餐具,又怕倒酒的时候会洒到客人。大部分客人都很有礼貌,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没什么存在感,因为很少人会正眼看我。虽然我知道这就是工作岗位本身的设置,但是时间长了,心里还是有点憋屈。
有一天,餐厅来了几个主管叮嘱要特别招待的贵宾,是美国来的航空工程师,听说在业内是很有名的。餐厅经理说我英语讲得比较地道,就派我去给他们点菜。跟客人聊了几句后,发现其中一位原来是我大学的校友,“相认”了后,他很直接的说没想到会有服务生教育程度那么高的。接下来几天,他们每次来餐厅,都会特地找我聊上几句,听我分享一下实习体验和大学的经历,也总记得我的名字。

求学耶鲁
这些互动,给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被尊重了。终于有客人看着我说话,知道我的名字,把我看作一个人,而不只是我的角色。但只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在美国读书吗?如果我没有高等学历,难道我就不值得被平等对待吗?
UWC是一个很倡导平等博爱的社群。然而,现实是,很多UWC的校友毕业后都会到各种名校读书,然后在一些“高精尖”公司或组织工作。UWC的学生在各个行业都很优秀——常青藤、牛津、剑桥、联合国、投行、咨询公司、无国界医生、创业家、博士......这些都是UWC毕业生常有的“光环”。但优秀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精英和排他主义。精英主义会让人冲昏头脑。即使是一些在慈善或助人组织工作的人,也很难避免出现一种“我懂的和拥有的比你多,所以我要来拯救你”的救世主心态。

在台大当交换生时的菲律宾好友们
这也有一定的危险,精英和排他主义也会引起社会不公。
大家是否听过古以色列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跟他的门徒说要“爱你的邻人(neighbour),如你爱自己一样。”然后门徒就问他,“那到底谁是我的“邻人”?”耶稣于是就讲了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话说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普遍歧视撒玛利亚人,觉得他们是外族(Gentiles),跟自己不一样。一天,一个犹太人被抢劫受伤,倒在路边。一个犹太教的祭师(等于现在的神父,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好人)经过,没理他。后来一个专门管理圣殿的利末人(也是犹太人,理论上应该也是好人)经过,也没理他。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动了恻隐之心,就把这个犹太人送到旅馆去,还给额外的钱给掌柜,叮嘱他好好照顾这个陌生人。
在这个故事里,到底谁才是那个犹太人的“邻人”?
这个故事让我经常重新思考“改变世界”的真义。
年前看到在香港又有内地游客受到歧视性辱骂和推撞,让人特别痛心。在内地出生,香港长大的我,在朋友圈上发了这条文字,引用在此,聊作结语:
无论肤色、宗教、种族、职业、社会地位,每个人都是“邻人”。形形式式的歧视,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地铁上拿着大包包的民工、习惯跟我们不一样的游客、放假时载歌载舞的外佣、离乡别井的外籍妇女、动作比较慢的服务生、话讲得不标准的外地人---有时候发现,他们都是我。
拿着三个大箱子挤在纽约地铁上的我、第一次去奢华场合不懂礼仪的我、在国外遇到朋友时兴奋得忘乎所以的我、在上海办事摸不着头脑的我、第一次在餐厅打工的我、在论坛上不敢发言怕被同学取笑我英语太烂的我:这些我,都好渴望有人可以给我多点理解、接纳和耐心,让我慢慢融入,也慢慢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
时过境迁,最近又遇到太多这样让人痛心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误解的事情。而我能做的,往往只是不参与这种集体歧视、集体言语暴力,能力所及时,可能给他让个座,主动指个路,看着他的眼睛讲话,或者给他一个微笑。才意识到这所奇怪的叫做UWC的学校给我的不只是一辈子的朋友和知识,还有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信念:我们是一样的。
有时候需要的只是时间,和一个“翻译”来让你我更好地认识彼此。我们很多生活在多元环境下的人(不只是国际化那种多元,还有城乡迁移、地域差距、熟悉好几代人的思维模式、不同行业的理解的那种多元),其实都是有独特视角和天赋的“文化翻译”,有一种作为不同世界桥梁的“超能力”。不要轻易放弃这份做和平大使的特权,为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做翻译,减少误会,增添差异带来的色彩。欢迎TA,就等于欢迎你自己。共勉。